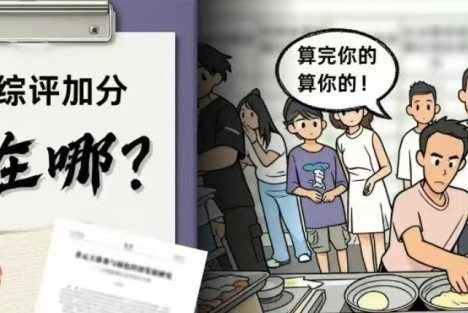秦明:钱学森“鲜为人知的一面”,正是他光辉伟大的一面
钱学森同志逝世16周年之际,又有人翻出了那篇在网络上流传过的文章《钱学森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不只是吹捧大跃进》:
列举了钱学森“和秘书互贴大字报”、“论证亩产万斤”、“为确保卫星唱响《东方红》,砍掉实验项目”、“批判张爱萍”等鲜为人知的过往。
看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行为语气,作者大约是想嘲讽钱学森“趋炎附势”、“攀附权力”吧,只是因为钱老的威望太高,不敢明言而已。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主要来自叶永烈在钱老逝世以后出版的传记作品《走进钱学森》及《钱学森》。
关于叶永烈作传、治史的态度,笔者以前曾经评析过,简而言之就是:半真半假、添盐加醋、春秋笔法、夹带私货。
关于揭示钱学森“鲜为人知的另一面”的原因,叶永烈在2019年《走近钱学森》修订版出版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指出:
钱学森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他也不得不在“大鸣大放”中与秘书互贴大字报,在“四清”运动中在工厂车间里坐在小马扎上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关于空间技术名词统一问题》这样的纯粹科学技术文件时不能不写上一段“最高指示”……
所以,叶永烈的目的倒不是为了“抹黑”钱学森,只是为了抨击那个时代。叶永烈的所作所为,不过是80年代以来的“非毛化”的延续。如果这个传记在钱学森同志逝世之前出版,钱学森同志绝对要站出来反驳他。
———1———
对于钱学森同志在大跃进期间论证粮食可以亩产万斤的文章,李锐和方舟子等人多次拿出来炒作,借此攻击钱学森、污蔑毛主席。
1958年6月,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文章
李锐在80年代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说: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刮的“五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主席”。“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叶永烈的叙事逻辑与李锐简直是一脉相承,都是将钱学森的行为栽赃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真实的历史却是毛主席是党内最先出来力纠“五风”的,对于宣传口放出的“亩产万斤”的“卫星”,毛主席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些在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中都有清晰记录。
1958年7月3日,毛主席批示:……每亩能收三百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二百斤增长百分之五十,何况还有三百五十到四百斤的希望。(《毛泽东年谱》)
摄影师舒世俊回忆,在列车上的省、地、县和生产队长会议上,毛主席听到粮食产量的虚报很不高兴。他突然问地方官员:“你们信不信上帝?”大家只是鸦雀无声地呆坐着,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不信,我信!”干部们惊呆了,没人吱声。毛主席说:“上帝是谁?他就是老百姓,是人民!你们把上帝惹翻了,非垮台不行!”
在反对浮夸风的指示无法贯彻的情况下,毛主席于1959年4月29日写了要求一直下发到小队一级的《党内通信》,明确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可见,毛主席绝对不可能因为钱学森的文章就信了“亩产万斤”的。
李锐大概发现他之前的谎言太经不起推敲,于是到了1991年他又改口说毛主席亲口说“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他的“证据”是在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期间:
“(关于)粮食放卫星的问题,我特意问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这篇文章对毛泽东固然起了作用,但当时毛泽东恐怕主要还是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者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李锐《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那么,毛主席到底是怎么看待钱学森的那篇文章的呢?
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风讯台》(《科学时报》前身)刊登了一篇题为《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的通讯录,记录了当年毛主席参观科学院展览会时与钱学森同志的一段对话:
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用两个小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科学院的展览会……毛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主席说:“我们还是1956年在政协见的面,你在青年报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的利用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
在这段交谈中,毛主席用“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对钱学森提出了委婉的批评,钱学森也作出了诚恳的检讨,承认了自己“不懂农业”、“计算方法也有错误”。
钱学森的确不是农学家,不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单说钱学森的物理推算,其实并没有什么罪过,理论论证过程还算严谨,只是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实际,才导致他得出的结论距离当时的实际情形相去甚远。
70年代举国一盘棋研究出了杂交水稻,水利、肥料等条件在毛泽东时代也陆续实现,今天我国杂交水稻的亩产已经提高到了1500公斤(3000斤),局地马铃薯的亩产更是可以达到5000公斤(1万斤),红薯产量则更高。当然,这是后话,钱老的文章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不好的作用。
最后,毛主席用“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化解了钱学森的压力,毕竟浮夸风的主要责任并不在钱学森身上,他也是被宣传口硬拉着搞了一篇“命题作文”。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在90年代出版的《忆毛主席》一书中回忆,毛主席曾找到吴冷西,让他顶住压力,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结果,吴冷西他们终究是没能顶住某些领导的压力。吴冷西忏悔说,“后悔当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2———
钱学森与秘书互贴大字报,让力学所的同志批评自己,秘书批评钱学森“太严肃,接近群众不够”,钱学森批评秘书贴“太孩子气”。
这件事放在“一团和气”、“服从领导”的今天的确是难以理解的,甚至认为这是钱学森在“表演”,“是科技工作者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委曲求全”。
然而,在钱学森同志自己看来,他就是在真诚地实行共产党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真心实意地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
一位从美国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并非偶然的。
钱学森从小就怀有家国情怀,目睹列强欺压积贫积弱的中国,立志学习知识,改变中国与世界。1929年他考入交大,选择攻读铁道机械专业,是为了“铁路救国”。
钱学森在交大读书期间因病休学,其间,读了很多科学社会主义的书。他在入党自传中写道:
“1930年暑假后因为我当时害了伤寒病,在杭州家里病卧一月余,体弱不能上学,在家休学一年。这一年是我思想上有很大转变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我脑筋里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
怀着“科学技术救国”的信念,钱学森赴美求学,尽最大努力学习、吸收各个领域有用的知识。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学森想要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用自己学习的知识为中国人民提供抗日的武器。然而,他对于当时腐朽的国民政府没有信心。冯·卡门也劝告他,说在美国做科学研究也能加强反法西斯的力量。于是钱学森继续留在了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做研究员。
在美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不仅仅是埋头做学问,还积累了广博的全球战略视野,为他后来成为中国人民的战略科学家奠定了知识基础。
在克服重重阻挠回到新中国以后,钱学森受到了高度的礼遇以及毛主席的亲自接见。见到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钱学森受到了由衷的触动,决心改造自己的思想,让自己尽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不眠不息地工作,在百忙之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并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科研事业,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生动运用使自己逐步成长为一名战略科学家。
1955年年底,钱学森在北京政协礼堂作了关于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科研工作,钱学森深有体会地说:
“我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20年,从科研工作中不断积累和认真总结的经验和科研方法,自感是行之有效的一套方法。回国后,学习了有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方面的著作以及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才恍然大悟,感到自己总结出来的那套科研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中都已阐述得很清楚了。”
1957年8月19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知识分子需要不断的改造》。他批评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不把劳动人民放在眼里,这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是很不利的。他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指出:
“科学研究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完不成的根本原因还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而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就使得人难于接近群众,不接近群众就丧失了力量的泉源。”
为了与为了与群众紧密结合,1958年中央号召“除四害”,钱学森认为这是接触群众的好机会,真的就跑到北京郊区农村一起参加。这件事很快被中央领导,批评力学所党委负责人说:“不能这么简单化地理解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的口号,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请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让他参加了。”
钱学森自觉地将毛主席的“两论”内化为自己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他说:
“我们要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来分析武器和尖端技术的发展过程。总是事出有因,有来龙去脉,这是可以分析研究的。这样,对武器的发展趋向,做到有个预见性。”
由此,钱学森提出了很多极具预见性的重大科研方向,例如前一段时间被网友翻出来的钱学森在1992年写给邹家华的信,他在三十多年前已经提出让中国预先研究新能源汽车,实现弯道超车。
钱学森还经常向其他科技工作者推荐如何学习“两论”,建议通过“掌握一般原理及方法”后在工程实践中积累经验以“再从理论上深入一步”,尔后再“回来搞具体应用”,进而实现“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目的。
通过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钱学森认识到“只搞自然科学技术不行”,还有比“打导弹、放卫星可复杂得多”的社会问题要去解决,于是就“去学社会科学”。于是,他在工作之余又通过十余年学习,不仅弄懂了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弄通了社会科学原理,啃下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留下了不少批注。
1975年反击“翻案风”的时候,钱学森贴了张爱萍的大字报,这是被很多知识精英诟病的历史问题,张爱萍之子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表达了很深的抱怨,甚至在1978年郭沫若逝世后,让钱学森接任中科院院长的提议直接被排除。
但这件事错的一方,真的是毛主席和钱学森吗?那么,为何张爱萍将军晚年在看到贫富分化的事实以后会产生深深的焦虑?在参观南街、小岗等农村地区后会发出如下感慨?
“用我自己的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见于《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
由此可见,说钱学森参加政治运动是“为了自保搞投机”纯属无稽之谈。
———3———
投机是什么?是那些在前三十年搞极左,在毛主席逝世后搞极右,还自诩“两头真”的小人们。
而钱学森同志对人民的忠诚,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自始至终从未发生过变化。
毛主席逝世之后,钱学森撰文纪念毛主席:“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
1987年3月14日,钱学森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赴英国进行友好访问,专程拜谒了位于伦敦的马克思墓并为中国留学生作了一场报告,他说:“中国300多年的历史证明,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在1989年发表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文中,掷地有声地回答: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不管今天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多少不尽如人意、不文明的现象存在,它仍不能掩盖共产主义文明的光辉。这种共产主义的最高文明形态仍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人类解放,特别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应该追求的崇高理想”。
1994年,毛主席诞辰101周年时,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与中国科学报社联合组织了一场小型研讨会——“毛泽东与科学”研讨会,学习和弘扬毛主席的科学思想。从《中国科学报》看到发言稿后,钱学森同志非常兴奋,立刻给《中国科学报》去信,提到了两点:《中国科学报》关于学习和弘扬毛主席科学思想的报道,以及关于创新精神培育和创新人才培养的报道非常好;希望《中国科学报》加强对科技创新问题和创新人才后续问题的报道。
紧接着,他又给王寿云等6位学者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毛主席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同志在与北大哲学系的教授们谈话时,更是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这样的钱学森,是包括叶永烈在内的那些站在劳动人民对立面的反毛小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
钱学森“鲜为人知的一面”,绝不是钱学森“不堪的一面”,恰恰是他不同于其他科学家的“光辉伟大的一面”。
一生忠于人民、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钱学森,无愧于“人民科学家”的伟大称号。

微信扫一扫,为民族复兴网助力!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