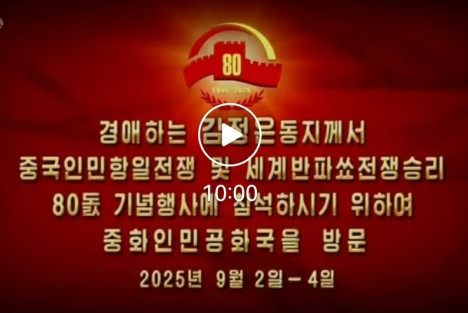《春回地暖》:成为革命复杂性的历史伏笔——土地改革题材经典文学札记之三
小说讲述西元1950年冬到1951年春,湖南省东部湘赣交界地区的回马乡土地改革运动的故事:县、区、乡、村干部和省里派来的土改工作队一起,克服一些农民的消极心理、土改工作人员缺乏经验和思想错误所造成的重重困难,镇压地主和国民党匪特分子的疯狂破坏活动,最终发动贫苦农民起来斗争,彻底打垮了地主阶级势力,取得了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
这部小说,在描写土地改革运动的文学作品中,是展现阶级斗争比较全面激烈的一部。在小说中,地主阶级中的顽固分子和潜藏下来的国民党匪特分子,对人民政权和翻身农民进行了一系列疯狂的反扑:它们暗中组织“贫民没收队”,“到处砍树木:栗子树,桕子树,茶子树,乱砍一气”;它们在各村散布各种谣言,比如“美国在朝鲜投原子弹啦,照死光啦”,“英国法国都出兵啦,广东广西都吃紧啦”,“斗完地主斗富农,斗完富农斗中农,共产党的政策就是要穷大家穷,天下只有贫雇农”,等等,以吓阻农民参与土改;它们挑唆被蒙蔽的农民趁夜烧粮仓;它们指使狗腿子向区乡干部打黑枪,下黑手,小说第一章,参加完土改培训的回马乡主席章培林,在返乡途中追拿偷砍茶子树的人,就被砍了一刀,而甘雨庙村女村长甘彩凤,则在土改即将深入时被地主甘文龙杀害;最后,地主和匪特甚至暗中聚会密谋,准备发起武装暴乱。
土改运动中发生如此多激烈复杂、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与这个地区的历史状况,以及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的。
小说中描写的回马乡地处湘东,曾是湘赣红色根据地的一部分,一度建立过革命政权,进行过打土豪、分田地,后来地主阶级卷土重来、反攻倒算,对农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农民先进分子则在共产党领导下与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牺牲惨烈,解放后“乡政府的烈士名册有厚厚一大本”。这个地方有革命的基础,但反动势力也很强大和顽固,是个“地主窠”。
另一方面,回马乡开始土地改革运动时,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际,国民党残余分子和地主阶级顽固分子以为能够借助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东山再起,它们纷纷蠢蠢而动,企图用恐吓、暗杀乃至武装暴乱的手段,里应外合颠覆新建立的人民政权。
这种历史和现实,就使回马乡的土地改革运动呈现出与其它地区迥然不同的状况。虽然解放一年多了,但回马乡的土改,某些时候甚至比北方地区在战争中进行的土改还要困难。
土改的困难,除了湘东的农民和其它地方的农民一样,“身上同样有着沉重的精神负担”之外,“还有个特殊情况是,正因为遭遇过二十年前一场残酷的屠杀,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更留有一种消极的痕迹,担心历史的重演”。小说用了不少的篇幅,塑造了一些“灵魂消极”的农民形象,比如:贫苦农民章木生胆子小,被地主狗腿子恐吓,不敢出面诉苦;贫苦农民章银生知道共产党给自己带来了活路,但是怀着“出头的椽子总是先烂”的心思,消极躲避,还阻止妻子出去参加土改工作;中农章东生糊里糊涂地被地主狗腿子章侯之骗进破坏组织,他犹豫彷徨,担心共产党呆不长,不敢举报;中农良富叔、章瑞生等思想落后,信谣传谣,对土改有沉重不安的心情。
困难也来自土改工作队内部。来回马乡开展土改工作的干部,“有地方上的,有县里的,也有省里的,集中学习的时间不多,思想一下子统一不起来”,研究工作时意见常有不一致的地方,导致一时无法步调一致地加强领导、开展工作。
因此,土改开头的回马乡,“群众简直像封冻的田野一样,沉闷,没有生气,地主不法分子的气焰却很嚣张,整个回马乡几乎成了谣言世界”。 面对种种困难和挫折,有些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情绪急躁,认为不必过多发动群众,要求人民政府出面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就行了。对此,区委书记李昌东指出:“土改靠谁来改呢?光靠我们这个工作队,再加上你们这些乡干部吗?当然不行!土改是群众自己的事,得由群众自己动手!只有把群众的眼睛擦亮啦,觉悟提高啦,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才打得倒地主阶级,拔得掉封建老根子!”这段话,说出了当年土地改革运动进行方式的基本政策思路,现在看来,意义深远。
要通过土改使农民“觉悟提高,真正发动起来”,以斗争的方式打下地主的威势是极为必要的过程。许多土改题材文学作品中涉及了这方面的情况,这部小说也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小说中写到,回马乡甘雨庙村大地主甘愚斋,财势雄厚,往日横行乡里,欺压农民,威风极大。土改开始后,他仍然气焰嚣张,被选为斗争的首要对象。
斗争会开始,甘愚斋“连脑壳也没有低,在他那张挤满黄斑点的粉白色脸孔上,摆出副满不在乎的神气。他把个水獭帽子捧在手里,靠香台边站着,一下接连一下地咽着喉咙。他那颗突出的大喉骨,也一上一下地滑动着,那一撮银白色的山羊胡子,也跟着颤抖个不歇气。”“‘诸位让我愚斋发表几句!’他开始说话了,搔了搔光秃秃的头皮,抹了一把正流出鼻涕来的长鼻子,声音低低的,就好像平常跟别人谈闲天那样。”
有农民斥骂他,他“还是抬起个脑壳,还是把一个旧水獭皮帽子捧在手里,摆出一副不死不活的神气”。直到农民气愤地抢下他的帽子,按着脑袋让他低头,扯烂了他的马褂,有人还喊着要脱掉他的裤子,“他开始发抖了”,“请诸位多多包涵”。
大家仍然斥骂,要动手,“他再不能保持那副不死不活的神气了”,“就索性装出副可怜相,蹲在那里,把一双手抖颤颤地抱着个光脑带,好像准备挨打的样子,长鼻子里淌出来的清水,沿着鼻尖直滴落到地上,嘴巴里还发出一阵细伢子似的唏唏声。”
村长甘彩凤号召大家“和他说理斗争”,并宣布姜部长和乡主席等工作同志都在场,甘愚斋才“服服帖帖把脑壳低下,直耸起两边瘦棱棱的肩胛骨”。
通过这样的斗争,才打掉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农民们消除了对地主势力的畏惧,章木生、章银生等曾经胆小怕事的农民也开始积极地投入改天换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当年的地主阶级和现在的公知们称这是“不人道”的“暴力土改”,但历史的事实是,这对国家和广大贫苦农民来说,正是最大的人道。
小说中描写了众多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历史和现实的种种言行,展现他们复杂多样的性格和在土改运动中的发展变化。
二十三岁的回马乡主席章培林是农民先进分子的代表。他的父亲在红军革命时期参加苏维埃政权贫农团,红军撤退后被还乡地主“挨户团”杀害,母亲带着两个细伢子逃进山里坚持斗争,“忍受了许多苦难和屈辱,“没有流一滴眼泪,也没有说一句鸣冤抱屈的话”。章培林继承了父母的坚强性格,嫉恶如仇,“解放后不到半年,培林就成为双减反霸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深刻的仇恨转化为坚强的力量,在斗争里显现出他的才能”,“给选作回马乡的乡主席”。
章培林“是个不大爱多话的人,开起会来说几句,也都很简短”,但有重要的事,也会说“很多话”。他为人正直,性格倔强,曾因混进干部队伍的富农分子章南山替反动地主说话,污蔑女村长甘彩凤,忍无可忍地打了他一巴掌,县委姜部长和区委书记李昌东批评他,让他向章南山道歉,他内心反复思量、斗争,认为自己没错,坚持不肯认错。
他工作认真,意志坚强。他的战友、恋人甘彩凤被地主分子杀害后,他很快抗住悲痛的冲击,坚持工作,并率队连夜冒雪长途追袭,抓回逃跑的暴乱地主分子。他是农村革命的新生力量。
乡农会主任甘金荣,二十多年前给地主当长工,受尽欺压,红军来了,他“参加了乡苏维埃,当上个土地委员”,“只可惜分配土地后,只种了一熟,刚过八月节,红军就撤退了,甘金荣先给反动派‘清乡队’抓起来,受了一场拷打,随后就脱身逃到南边‘洞’里跟着苏维埃死守了两年。那两年日子,大家吃石蛤蟆,啃蕨根树皮,跟白军打了不晓得多少仗,他甘金荣带花受伤也不止一次。后来,红军放弃山洞,翻山越岭,过江西上井冈山”,他因伤病留下,失去组织关系,在江西修水给地主打了几年长工,回到家乡,给本村地主甘愚斋打长工,“事到如今,只好咬咬牙熬着,想不到,一熬就熬了十多年!”
解放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政权的基层中坚力量,被选为乡农会主任,反霸剿匪、支援前线,他是乡村农民力量的组织领导人物。他为人沉稳,意志坚定,女儿甘彩凤被暗杀后,他忍着巨大悲痛继续帮助工作队推进土改运动。他是革命斗争历史和现实延续、发展的象征。 区委书记李昌东是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南下干部,为人朴实,与农民亲密无间。小说中曾以白描手法刻画了他的形象:
他去太平塘村,遇到章培林等人正在田里“洗花生”(收花生),他先是站在田塍上询问“收得几担”、“回马乡有几多头耕牛”,“又问到田亩,问到茶子山,问到红薯、花生、甘蔗和茶子树”,然后“脱掉鞋袜,卷起裤脚管,也跨下田来了”。他先使用牛拉耙子“沿田边耙了一阵”,又用筛子捞花生荚子。边劳动,边与章培林聊起乡财粮委员章南山的问题,要章培林“注意他的行动,多听听群众对他的反映”。干了一会儿,他“把筛子还给乡主席,自己上了田塍,也顾不上洗脚,只把鞋袜往胳肢窝里一挟,就跟大家告辞……向他们扬了扬手,跨开步子,一迳朝太平塘走去”。
这段,生动地表现了李昌东这样的基层共产党干部及其所代表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性。
李昌东这样的干部,具有革命经验,革命意志和阶级意识都很强,但仍难免在工作中犯错误。回马乡土改最初阶段,他“要求诉苦诉得普遍,诉得彻底,强调先完成诉苦阶段,再来发动斗争”,当群众有开斗争会的要求、章培林等乡村干部也建议用斗争会的方式发动群众时,他却认为斗地主要“师出有名”,要“等火候”,这客观上造成地主“还在村里大摇大摆的”,贫苦农民“大家心里犯顾虑,都怕话说早了,会传到人家地主分子耳朵里去”,因而连诉苦阶段也没法完成,地主分子则砍树、造谣、打黑枪甚至杀害干部,气焰嚣张。李昌东后来检讨自己犯了“经验主义小手小脚的毛病”,有“怕乱套的思想”,他知错即改,带队入驻难度最大的村开展工作,坚决支持贫困农民清算地主的剥削账,很快打开了土改的局面。
土改工作队员杜放是个大学生,虽然容易激动,缺乏工作经验,但他朝气蓬勃,全身心拥抱革命,自觉地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很快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喜爱。
而土改工作组组长肖一智则是另一类知识分子。他宣称“理论指导行动”,但只是照搬书本,理论不能联系实际。他在群众会上只会照本宣科,给农民“上大课,讲政策,把土改法从第一条讲到末一条,一字不漏地讲给他们听”,许多农民听不懂,在会上没有反应,到太平塘村的“头一炮”就失败了。他也说尊重群众,但其实内心蔑视农民。受了批评,感到不被重视,他就消极对待土改工作,斗争越开展,别人愈热烈,他就越冷淡,越消沉,却认为“自己给挤出了斗争的漩涡”。对镇压罪证确凿的反动恶霸地主和匪特,他认为不符合“崇高的人道主义的原则”。最终,他借口看病离开工作队,成了土改运动的逃兵。可以想见,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在用“理论”影响革命进程失败后,必然成为革命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如果活到现在,一定成为党内公知。
小说中还描摹了各类地主分子的形象,例如笑里藏刀的章耕野,粗蛮凶残的甘愚斋,讲究“风雅”的金仲甫,刁顽无赖的女地主箭大嫂,等等,在不同性格的言行中展示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
与其它同类题材文学作品相比,《春回地暖》这部小说在土地改革运动胜利的凯歌声中,添加了某些阴郁之调:小说最后写到,满怀仇恨的女地主箭大嫂,在暗夜中跑到被分给贫苦农民章木生的田里撒盐,“要害得木生种不得田”。而地主章耕野对自己儿子的一番“阶级教育”,更是令人深思。
章耕野是回马乡地主阶级发号施令的“王”。二十年前,他参与“清乡”,杀害农会人员,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军队中杀害过被俘的新四军女战士,后来退伍回乡。解放前夕,他“晓得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不长了,就装出副假仁假义的样子,处处讨好人,笼络人”。解放大军来了,他当“迎接解放支前委员会主任”,进行支前工作,征伕送粮。但暗地里,他组织“中国人民湘赣边区剿共游击纵队”,美军仁川登陆后,曾图谋“抓住这个难得的好时机,组织一次全区性的大暴动,杀掉那姓李的山西佬区委书记,夺取枪支,拉起队伍上东面湘赣边境的连云山”。土改开始,他指使狗腿子搞破坏,散布谣言,并谋划杀害区乡干部,制造反革命的恐怖气氛。
土改中要求地主向贫苦农民退还榨取的租粮,首先拿章耕野开刀,打下了他的气焰。他狗急跳墙,密谋暴乱。临走前,他对自己那个大学毕业的儿子谈话,把白天前来退租的贫苦农民称为“强盗坯子”,让儿子“要仔细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说“我们祖孙三代,都是本份人”,“从来冒做过么子伤天害理的事情”,“时势是这样的时势,就像共产党说的是‘阶级斗争’嘛,你有么子办法呢?”他叮嘱儿子:“今后,你一定要作出顺着共产党的样子!共产党要分我们一家的田地房产,留给你一斗就一斗,一升就一升,住得一间牛栏房,就住一间牛栏房……当心不要吃眼前亏……”
女地主箭大嫂的破坏行为和章耕野的“阶级教育”,在当时印证着“不忘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而现在看来,作者不经意间埋下了革命复杂性的历史伏笔:章耕野狗急跳墙自取灭亡了,那个接受了他“阶级教育”的“有文化”的大学生儿子,以后会是怎样的呢?有可能,他在新中国的社会环境教育下成为像革命烈士彭湃那样背叛自己大地主家庭的真正革命者;也很可能,他牢记爷老子的“阶级教育”,“不吃眼前亏”地暂时“隐忍”,到“历史转折”后凭着“大学文化”的资本成为“教授”、“学者”、“作家”之类,时不时发表一些“学术论文”阴暗贬斥土地改革运动,或者写出“软埋”之类的“小说”、制作“生万物”之类的电视剧,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涂脂抹粉。四十年来的某些“著名”公知,很可能正是“章耕野”的孝子贤孙呢。
这部小说的作者王西彦,西元1935年在北平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左联”革命文艺活动,西元1938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战地做抗战宣传工作,后来回到家乡浙江金华,曾参与共产党和进步人土主持的文化宣传工作,西元1942年辗转于广西、福建、湖南从事学校教学并文学创作,西元1950年被选为长沙市文联副主席,后以土改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湘东平江老苏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写出反映土改前后农村状况的散文报告集《湘东老苏区杂记》,以此为主要素材于西元1962年创作完成长篇小说《春回地暖》。
这部小说以白描手法和心理描写相结合,具有较强的艺术效果。小说对农村生活描写细致,人物语言以湖南方言为主,乡土气息浓厚。王西彦在书后《关于〈春回地暖〉答读者问》中写到:“一九五O年和一九五一年,我先后两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第一次的地点是湘东老苏区,第二次是皖北老根据地。”深入生活,艺术地表现“一场伟大的革命”,这是当年愿意投身革命的作家的共同道路。

微信扫一扫,为民族复兴网助力!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