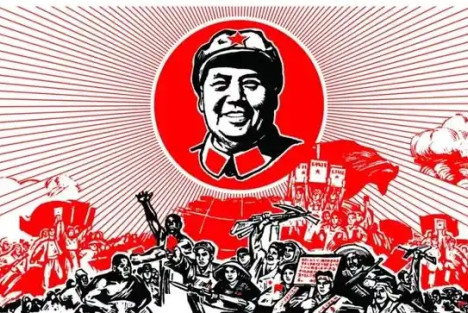欧洲金靴:我们都是预制菜
预制菜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必然产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业文明演进进程高阶、城市能级历史大跨越的某种象征,日本、韩国、香港、中国大陆等地的发展均为其例。
因此,看预制菜产业必须看到它的两个暗面——
① 成本层面,对房租(地价)的趋附性;
② 效率层面,外包模式的餐饮领域实践。
1
第一点很好理解。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主要城市的土地相关成本(包括购买、租赁、商业运营等)经历了至少两个数量级的增长。
这构成了所有依赖城市物理空间的商业活动,尤其是餐饮业所面临的严峻经济背景更是显例。
对于餐饮业而言,租金、人力、食材是三座成本大山,其中商铺租金往往是最刚性、占比最高也是最无法避免的成本,那么能够被牺牲的只能是人力和食材,餐饮业态被迫向“去厨师化”和“去厨房化”演进,预制菜应运而生。
以上大多是B端(供给端)的痛苦,而C端(需求端)的痛苦同样是加速预制菜诞生发展的推动剂——不断升级的地价推高房价和房租,迫使大量低收入人群远离核心区域居住,又因无力承担“大House”的购价,由此产生了两个现实:通勤时间过长(快节奏导致用餐时间压缩)+家庭厨房狭小(制作餐食并不方便)。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有过一句揭露:
尽管中产阶级化可以带来城市经济的复兴,但其实这仅仅是将穷人驱逐或者分离的结果罢了。
这,同样加速预制菜的市场需求膨胀。
2
再说第二点:外包模式。
预制菜实际就是店家将餐食制作环节交付于第三方,即外包模式对餐饮行业的侵蚀、渗透、运用。
因此,一切关于预制菜产业的“恶”、消费者对预制菜所有的抵触,事实上都是外包制度恶性一面的又一次展现。
从青岛大学“被外包”的张大爷,到如今无法回避的餐饮业“被外包”的预制菜——万物皆可外包的世界,每个人的生命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洪流中都有可能沦为“外包化”的流水线螺丝钉。
餐家的营业店面是租来的,随时有可能面临房东的涨价或驱逐;制作的菜品是早早买来速冻的,随时有可能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前来取餐的外卖小哥是外卖平台“众包模式”兼职的,随时有可能急于配送而闯红灯出车祸但平台无需承担任何风险(甚至从一开始连社保都不用交)……
看吧,所有人都处在这套“算法系统”里,每一层都有可能是“被外包的”。
原子化的社会,主体性必然消亡,各要素都会难以逃脱的“他者”化。
用2022年末流行的那句话说便是: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面对利益时没有遗漏没有放过,面对风险时亦是没有责任没有义务,不得不说,外包模式这可真是人类商业史的“伟大发明”……
已几乎难以追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立并使用外包模式是何时、哪家公司、什么行业,但以企业为主导单元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外包成熟使用的,应该是福特,已逾百年。
外包的本质是拓宽生产链条,将供应链“固态化”,从而实现对人力成本的最小化控制。
福特曾经有过内部计算,没有投入安全设备的话,公司因赔偿事故遇难的损失为$49.5 million,而投入安全设备、修复安全隐患的总成本则为$137 million——资本果断选择前者。
百年来,从区域外包到离岸外包,全球化的实质同样正是一场“外包的盛宴”。
有的国家和族群攫取最大的利益并付出最少的劳动,而有的国家和族群拿着最微薄的报酬却付出最惨痛的代价,或是生理剥削、或是尊严剥削、或是环境剥削。
他们可能是赤道雨林里的橡胶工人,也可能是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比德县的甘蔗女工;可能是中东国家穿梭于城市天际线之间的南亚渡客,也有可能是富士康大楼天台的农民工们……
娜奥米·克恩在《No Logo》中一语中的:
品牌公司通过外包剥离生产责任,同时用营销掩盖供应链中的剥削。跨国资本专注品牌营销,将生产外包给血汗工厂,以此切割道德责任。
3
社会保障的缺失,劳务主体的模糊,以及风险责任归属的含混,让外包制度下的工人成为了“无主之人”,他们在劳资关系中既“无主”也“无我”,谁都能雇佣他们,谁也能抛弃他们。
恰似两个月前青岛大学的那封说明书里,默默离去的张大爷连姓名都不配拥有,只是以冷冰冰的“物业工作人员”这个几近工具人的被物化姿态出现在官方的声明中。
一包又一包程序化生产的预制菜何尝不是如此?
每一包都叫做“辣椒小炒肉”,每一袋都写着“梅干菜扣肉”,每一碗都印着“精品酸菜鱼”……
千篇一律,严禁个性。
今天的互联网快递外卖平台与福特一样,当然不会“傻了吧唧”地多招快递员、外卖骑手、多发奖金、多缴社保……
它们不但会大批量使用外包模式,还必须把骑手数量控制在成本量级内,既能让骑手不得不疯狂闯红灯,又能让闯红灯带来的事故风险被降到一个资本可接受的范围。
除却风险管控,在利益分配层面,更是体现着严格的系统控制。
拿网约车为例,无论司机每天多么努力,每小时平均收入无限趋近于三十元,运气好点能接到一个长途大单,但是返程往往接不到客;当你前面几个小时收入不错的时候,后面几个小时直线下降……
算法可以用回归和拟合控制收入曲线。
被平台“外包的你”或许可以跑得赢红绿灯,但绝无可能跑赢算法。
实在不行,平台们还可以把风险转嫁到消费者即用户身上,明明是资本方压榨工人阶级,却要让市场承担由此带来的不良使用体验。
去年初,同是阿里系下的另一家巨头零售在面临增长乏力的改革压力时,同样选择对最底层的工人进行“改革”,其分拣员曾对外透露:
(改革)就两件事,一是正编工转三方,二是降薪,如果不转,就会被叫去谈话,分配的任务也会变少。
在利润难以满足资本需求的情况下,工人群体永远是最快捷迅速又简单粗暴的降本承受者。
这就是前年的电影《年会不能停》里讲述的“先进公司”所谓“先进管理模式”(片中的“广进计划”),一方面大量使用外包人员,一方面大规模裁撤在编员工,以实现所谓“转型”。
青岛大学那位被拖欠八个月工资的张大爷,只是最新一例悲剧罢了,但他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4
同时,对于外包的另一面:用工方,这种模式同样存在着隐性的、抗压层面的结构性危机。
以“体制内”性质的青岛大学来说,当前,外包在大型央企/国企、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政府机关/国资企业早已十分常见。
政务部门习惯性将业务外包给市场上的商业公司,通过竞聘角逐选择出最物美价廉的合作方,再打造出的最优质的产品或完成城建项目的落地。
还记得三年前面对疫情肆虐登时陷入大面积瘫痪、基层行政单位在一夜之间近乎崩溃的上海市吗?
自民国时期的孤岛时代开始,上海的市政治理体系就一向以“效率”著称,然而2022年时为什么会在面对“集体团战”的现实需求下,出现体系式崩塌?
原因就在于,上海市政府包括各区政府,是中国“最会外包”也是最早外包的省级政府单位,也向来坐拥国内最优秀的外包业务资源和最丰盈的外包人才规模。
早在世纪之交,浦东新区就开始在社会服务(养老事务、残疾人事务、妇女事务)、城市管理(绿化养护、河道保洁、垃圾分类)、专业维护(政务网络、绩效评价、数据分析)、公共文化(博物馆、公园等运营)等方面尝试外包模式,上海也是最早建立制度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形式的城市。
这种行政管理模式在和平时期自然利处明显,尤其在刺激经济活力、推动市场主体主动性方面,也是上海所谓“效率”“前卫”“先锋”的城市文化和市民气质的培塑源之一。
但是,这种外包体系以及长久塑造的外包思维,在陷入战争状态时,就会瞬间暴露并随着战时状态的烈度发展而放大其结构性缺陷。
比如,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岗位的官员长期不做实事、习惯于“验收”“审核”“批阅”,导致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准日日下滑,待到突发危机时根本应付不了任何局面——三年前那些在镜头前各种丑态百出的官员,毫无疑问和平时期都是端坐办公室侃侃而谈的懂王,却全部在战争面前现了眼。
不得不说,这是许多一线城市政府和大型央企/国企的通病。
三年前,当各企业/市场主体全部休业时,上海市从市府到区府各级别官员的抗疫指挥能力、一线作战能力、物资物流统筹能力均低得令人发指,既不会亲自上阵干活,也不会组织依靠群众,完全比不过很多三四线小城的基层干部。
那些中国所谓“下沉地带”日日俯首甘为孺子牛、卷起裤管下泥地的勤务员们,或许没有统筹规划万亿级别城市发展的视界和格局,也没有能力与马斯克们谈笑风生,但是在区域性公共灾难面前,他们远比那些在大城市身居高位的高级大员们更能服务和保护群众。
中国人民在面对天灾时常常唯一的期盼就是解放军,再大的困难,只要看到解放军一到便立刻恢复信心。
这种其实说不上来道理、完全说不清道不明的对解放军的天然信任感,究竟从何而来?
原因很简单,解放军(或者说国防军事领域)是当前我国为数不多的绝对永远不可能“外包”的净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不可能有“雇佣军”,我们的人民军队一定是百分百站立在党旗下、百分百誓死为人民服务的(2015年军改和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更甚)。
这就是“零外包”带来的军民鱼水情。
2025年夏天,贵州榕江抗洪
2021年夏天,河南郑州抗洪,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政委朱生岭(上将军衔,曾参加2019年阅兵),与战士同赴一线作业
跋
就历史脉络而论,从80年代中期的“党政分离”,到90年代末的国营经济体系瓦解,再到入世之后城市化进程下的东西部区域不平衡——集体主义叙事的坍塌,其摔落和挥溅的尘土会弥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外包模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物或偏狭范围内的专业概念,它是诸多历史事件演进进程中所逐步形成的产物。
它携带着时代的记忆,也诉说着太多心照不宣的变化。
就像电影《年会不能停》里那句无情又傲慢的谑语:
时代的列车开过去,总会有人在车轮子底下增加摩擦力呀…
那些车轮子下的人,就是一个个「人型预制菜」。

微信扫一扫,为民族复兴网助力!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